找不到好工作,大学还有什么用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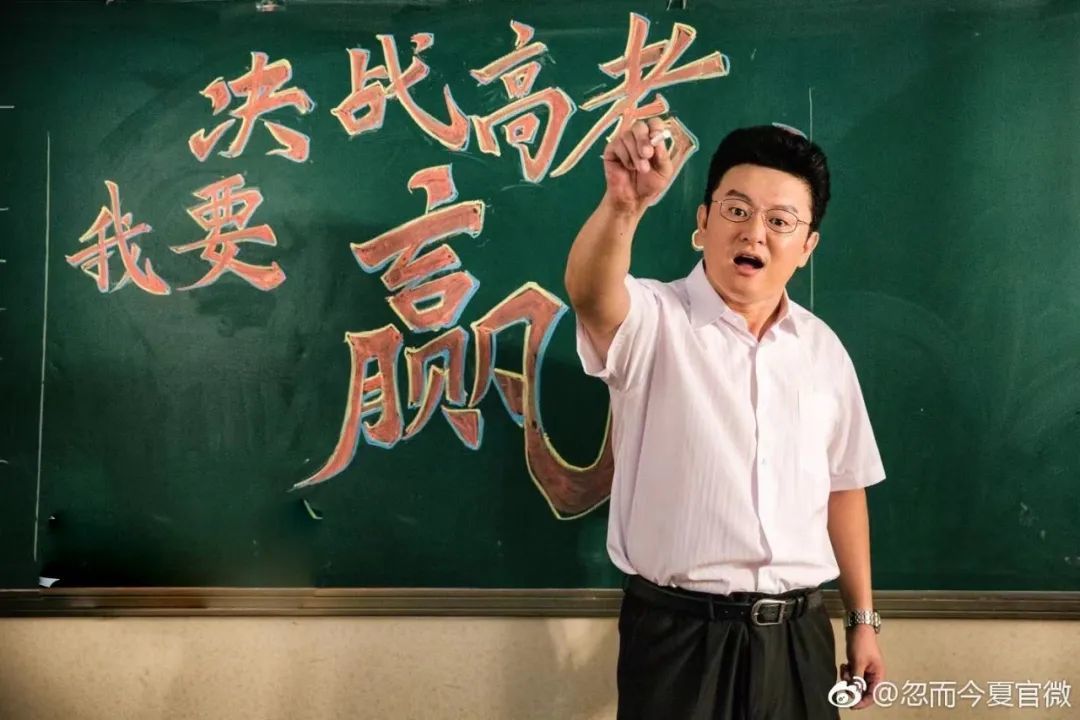
《二十不惑》剧照
如此一来,大学同中小学、研究实验室、学术协会、博物馆等机构相比,特殊之处是什么?
在大学里,本科生初次接触适于不同学科的探索模式。理想情况下,他们不仅掌握了大量信息,还应该具备挑战人类对某一课题的既有理解力并加以扩展的能力。
科利尼认为,相比于中小学教育所有人,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培养未来学者和科学家。但这需要学生们掌握独立自主性,需要接触科研工作的范例,做出自己的作品,对特定学科工作有所了解。“仅仅勉励他们去追求真理、培养准确性、清晰地表达自我,则是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。”
高等教育近几十年来累积的变化,通常被概括为:“它将服务目标从‘精英’转向‘大众’;它还有一种我认为应该抵制的倾向,即把‘无用’的科目与‘精英’相提并论,把‘有用’的科目与‘大众’等量齐观。”但科利尼认为,我们应该欢迎一个真正民主的高等教育体系,这样它才会持续存在,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。
关于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的论调,并不专属于当代。19世纪以来,批评家、改革者和政府官员们都声称,大学所做的研究是“无用的”,他们认为,大学开展的研究,应该更直接、有效地服务于国家需要。
19世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约翰·亨利·纽曼曾指出,大学的重点在于博雅教育。若仅把大学视作各个学科的拼盘,那么大学就会沦为“集市”,或伦敦的家具大卖场,各种商品杂乱地堆放一处,在相互独立的摊位上出售。“大学教育不仅让人清醒地认知自己的观点和判断,还能让人正确地发挥之,雄辩地表达之,有力地强调之。这种教育教人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,直奔主题,理清杂乱的思绪,明辨诡辩的成分,摒弃无关的信息。”
但科利尼认为纽曼把标准定得太高了。一个人在18岁左右,进入大学某个专业学习三、四年,真的可以达到以上的目标吗?“他并不描述学生学到了什么,也不提及学生具体获得了怎样的技能,而是更多关注学生和知识的关系,他们处置知识的方式,以及他们判断自己的知识在广阔人类理解版图中的位置的能力。”科利尼写道,“纽曼所勾勒的教育理想是诱人的,但也是异常空洞的。”
在这场论战中,“修辞泛滥”是常见的特征。教育和培训不同,但修辞泛滥总是会指向人类最理想的品质,文明社会的愿景和对人生目标的高谈阔论。
科利尼强调的是,社会教育下一代,不是为了让他们为经济做出贡献,而是为了让他们延展、加深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理解,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职业所需的有用的知识和技能。
尽管科利尼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确定的答案,但他更清楚大学不是什么。至少从英国官方角度看,大学不再是富家子弟的社交俱乐部,也不再是培训英国国教牧师的神学院。
就大学来说,无论开展何种程度的专业或职业“培训”,其支配性目标都是通过自由探索来提升人类的理解力。
科利尼认为,当我们问“大学有什么用”时,就像在问“国家有什么用”“爱情有什么用”类似,都会把一项复杂的活动或机构,简化为单一而狭隘的用途。
“最明智的做法,可能不是对狭隘的问题穷追不舍,而是让思考自行蔓延,沉思可能被某个术语遮蔽的多样性,斟酌一系列的描述和界定方式,或揣摩种种历史实例,而非寻求单一的、决定性的观点。”

